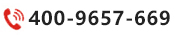中國文學(xué)外譯:基于文明與對話
《中國文學(xué)外譯:基于文明與對話》由派斯翻譯于2017/08/02整理發(fā)布,如需轉(zhuǎn)載,請標(biāo)明出處
點(diǎn)擊量:
中國文學(xué)外譯是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戰(zhàn)略的優(yōu)選路徑與重要內(nèi)容。隨著該戰(zhàn)略進(jìn)程的深化與發(fā)展,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期待與高水平文學(xué)翻譯人才匱乏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,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究竟應(yīng)該由誰(國內(nèi)譯者或國外譯者)來承擔(dān)的問題亦隨之日趨突出。從翻譯學(xué)角度看,中國文學(xué)外譯戰(zhàn)略的譯者選擇之所以成為“問題”,顯然受困于其間存在的兩個(gè)預(yù)設(shè):一是在語言素養(yǎng)方面,國內(nèi)譯者與國外譯者之間存在差異;二是在翻譯理念與策略層面,國內(nèi)譯者與國外譯者之間同樣存在差異。
譯文表達(dá)的地道性焦慮
對于由中國譯者承擔(dān)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的觀點(diǎn)或做法,很多學(xué)者持否定態(tài)度,他們較為推崇國內(nèi)外譯者共同翻譯的模式。在翻譯過程中,外文表達(dá)的地道性是最為直觀的考量因素,文學(xué)作品尤為如此。然而問題是,我們似乎由此產(chǎn)生了一種基于譯文表達(dá)地道性的焦慮,過于張揚(yáng)語言表達(dá)因素在中國文學(xué)國際化進(jìn)程中的重要作用,從而使得中國譯者信心不足,甚至畏懼不為。
毫無疑問,影響中國文學(xué)國際化進(jìn)程的因素較多,整體上呈現(xiàn)為一個(gè)四維系統(tǒng):第一維度,國際大語境的制約;第二維度,包括經(jīng)濟(jì)、軍事實(shí)力等在內(nèi)的中國硬實(shí)力影響,以及包括文化、政治、外交政策等在內(nèi)的中國軟實(shí)力影響;第三維度,國外讀者基于自身文化與價(jià)值觀理念而形成的社會(huì)性閱讀傾向;第四維度,作品自身質(zhì)量釋放的閱讀行為驅(qū)動(dòng)力。在這一系統(tǒng)里,譯文表達(dá)的地道性因素歸屬在作品自身質(zhì)量維度中(語言質(zhì)量)。至于該因素在中國文學(xué)國際化進(jìn)程整體環(huán)境系統(tǒng)中究竟占多大權(quán)重,甚或能否產(chǎn)生終極性影響,這里無法通過科學(xué)的實(shí)證研究獲得相應(yīng)數(shù)據(jù),只能通過對其他幾種因素的解析,從而形成較為客觀的認(rèn)識。
首先,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優(yōu)越論仍在影響著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(xué)作品的閱讀沖動(dòng)。其次,中國現(xiàn)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自身的缺陷或不足。例如大多作品缺乏對所經(jīng)歷時(shí)代全面而深刻的表達(dá)、不注重人物的深度刻畫或描寫、節(jié)奏拖沓等。再次,文化與價(jià)值觀理念指的是一定主體在特定社會(huì)與文化語境中獲得的決定、支配自己行動(dòng)和決策判斷的總體信念,它具有實(shí)踐品格,通過“為我所愛”與“為我所用”兩種意圖而產(chǎn)生驅(qū)動(dòng)力。最后,讀者的閱讀興趣、方式雖然存在跨時(shí)空差異,但其重心可以落實(shí)在語言層面,并且有可能超越語言層面。例如,對于《哈利·波特》等流行作品的及時(shí)翻譯,雖然有時(shí)粗糙不堪,卻可以滿足讀者對故事情節(jié)及時(shí)追求的期待。
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,在通常情況下,語言表達(dá)的地道性這一因素會(huì)在國際語境潮流、民族文化意識、消費(fèi)文化轉(zhuǎn)型等的沖擊下被有效消解。因此,譯文表達(dá)的地道性焦慮癥顯然過于極端,在某種程度上會(huì)削弱中國文學(xué)國際化進(jìn)程的源動(dòng)力。
翻譯實(shí)踐的人文社會(huì)性
翻譯從根本上是文本和譯者關(guān)于詩學(xué)、意識形態(tài)和歷史的一種協(xié)商,因此,人文社會(huì)性是翻譯實(shí)踐的基本屬性。文學(xué)翻譯是翻譯人文社會(huì)性的經(jīng)典鏡像,中國文學(xué)由誰來譯“問題”基于語言素養(yǎng)的考量,其局限性就在于,這種結(jié)構(gòu)主義方法論實(shí)際上掩蓋了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的歷史價(jià)值評判或?qū)徝辣磉_(dá)問題,即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的意圖和功能。
這就有必要對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的社會(huì)語境進(jìn)行考察。一方面,社會(huì)已經(jīng)成為全球范圍的歷史性存在,這必然呼喚著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視野與人文關(guān)懷。但另一方面,從20世紀(jì)90年代始,世界上不同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重心已經(jīng)由傳統(tǒng)的以經(jīng)濟(jì)手段和軍事資源為主的硬實(shí)力轉(zhuǎn)至以文化為核心要素的軟實(shí)力, “軟實(shí)力”競爭本質(zhì)上張揚(yáng)的是不同國家自身民族文化、意識形態(tài)等方面的吸引力。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應(yīng)該是全球化語境下從事人文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研究必須面對的一個(gè)大問題。
在此前提下,中國文學(xué)外譯就獲得了定奪其理念與策略所依賴的意圖或功能:一方面立足中國文學(xué)文化的推廣,積極為“世界文化”、“全球知識”作出貢獻(xiàn);另一方面則要認(rèn)清當(dāng)下中國文學(xué)外譯作為國家敘事或戰(zhàn)略的本質(zhì),提升我國文化軟實(shí)力。在這種張力的作用下,中國文化借文學(xué)外譯而“走出去”的戰(zhàn)略其理念應(yīng)該是在多元文化對話和交流的框架中,既維持中華文化的差異性,又融納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共性,進(jìn)而更好地塑造中華文化形象與價(jià)值屬性。
中國文學(xué)外譯的文本選擇
對于中國文學(xué)外譯戰(zhàn)略而言,如果選擇國外譯者承擔(dān)中國文學(xué)外譯任務(wù),除了他們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可能不如國內(nèi)譯者更為準(zhǔn)確與深刻外,還可能存在學(xué)理上的憂慮。其立足點(diǎn)就在于,包括譯者在內(nèi)的語言實(shí)踐者是社會(huì)中的個(gè)體,自然地處于對張揚(yáng)自身價(jià)值觀與傳達(dá)原作者價(jià)值觀的雙重本能之下,會(huì)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表達(dá)出自己的語言偏見,并以一種“話語者態(tài)度”的表象模式控制著文本與翻譯策略的選擇。
基于此,國外譯者的中國文學(xué)外譯實(shí)踐能否主動(dòng)或有意識地在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尋求并實(shí)現(xiàn)平衡,能否推動(dòng)中華民族優(yōu)秀文化產(chǎn)生國際性影響,從而提高我國文化軟實(shí)力,需要冷靜思考。從文本選擇角度來說,中國文學(xué)外譯需要注重世界話語,同時(shí)更要堅(jiān)定民族文化自信,為此就要盡量選擇那些能夠向世界推介并闡釋那些具有中國特色、蘊(yùn)藏中華思想文化與民族智慧的故事或作品,它們才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最佳材料。一味迎合西方讀者的所謂市場原則,雖然會(huì)在一定范圍或程度上較易“走出去”,但就其軟實(shí)力效能而言,則會(huì)直接損害我國在國際社會(huì)的聲譽(yù)與形象,并且同時(shí)遮蔽原作中滲透的中華本土經(jīng)驗(yàn)和民族文化特質(zhì)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方人對于中國文化、中國形象的認(rèn)知錯(cuò)誤或混亂,從而產(chǎn)生負(fù)面效能。
在全球化時(shí)代,翻譯的功能得到了新的拓展,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張力強(qiáng)化了文化外譯對于國家利益與文化的建構(gòu)作用,同時(shí)也能夠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重新設(shè)定世界文化格局。高層次文學(xué)外譯人才的匱乏已經(jīng)成為當(dāng)下中國文化“走出去”進(jìn)程的瓶頸,我們必須清醒認(rèn)識到,這一問題的解決應(yīng)該放置于中國文學(xué)外譯戰(zhàn)略的整體系統(tǒng)中,在先驗(yàn)性批判或經(jīng)驗(yàn)性認(rèn)知的基礎(chǔ)上加以重新審察與處理。“講好中國故事”需要注重譯文表達(dá)的地道性,需要關(guān)注外國人的興趣與能力,但根本上必須在全球化框架下以文明與對話為基礎(chǔ)進(jìn)行翻譯策略的科學(xué)設(shè)計(jì),在本地化翻譯思維和世界性文化傳播中尋找基于文學(xué)功能、世界文明與民族身份的有效平衡。
《中國文學(xué)外譯:基于文明與對話》由派斯翻譯于2017/08/02整理發(fā)布,如需轉(zhuǎn)載,請標(biāo)明出處